| 摘要:在求学的十几年时光里,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不同性格、不同学养的老师也有很多,然而,在众多老师中印象深刻的只有那么几位。 一 我的小学,在村子最东头,从马路下来过桥就是…… |
在求学的十几年时光里,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不同性格、不同学养的老师也有很多,然而,在众多老师中印象深刻的只有那么几位。
一
我的小学,在村子最东头,从马路下来过桥就是。学校虽小,却也几经变迁。最初校门临大路,是红色木门,漆色斑驳,像一个历经岁月沧桑的耄耋老人在村口颓然站立。门轴较高,下面露出很大的缝隙。上学去得早时,大门紧闭。我们就在门缝里钻来钻去,那时的我们并不急着进教室学习。
后来大门进行整修,木门悄然隐退,漂亮美观的铁栅栏门赫然耸立,上面排列着尖尖的刺。去得早的同学对此望而生畏,不敢越大门半步。

再后来村里有权势的大户把临路的土地占为己有,建成漂亮的两层小楼,学校瘦了半边,大门被挤到不易觉察的长长的甬道的尽头。
村小学的老师大都是民师。小学二、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姓谢的老先生。谢老师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微胖,寸头,头发稀疏。下巴的胡子茬很清晰,如果像古人一样蓄起胡须来,应该是个大胡子。
路边有我们家一块田地,记得小时候收麦子,麦子装满一架子车后,父母亲和哥哥妹妹都回去了。留我一个人在那看守余下的麦子,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恐惧和黑暗一起围拢过来。
我不知道怎样打发这漫长的时光,不知道把目光停留在何处。我尝试不去看不远处的宗族的坟地——那里有我不曾谋面的家族长辈,也有曾经朝夕相处的叔伯。但我还是担心会有不期而遇的鬼魅,于是也偶尔向远处眺望一下,后来我甚至轻轻地哼起了歌。天知道,我那时有多害怕。
好在有惊无险,直到父母亲再次回来,我的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我至今都不明白留在那里看守麦子的为什么是我,虽然曾经因独处而心怀恐惧,但是那次经历让我不再相信别人口中所谓的鬼神。
谢老师每天总是骑着他那辆二八自行车在田野中穿梭。农忙时节,谢老师总是满脸通红,脖子里搭条干活的毛巾,气喘吁吁地来上课。也许是那样子太像一个干活的老农,有调皮的学生就私下喊他谢老头。
谢老师上课很认真,不认真听课的会受到批评。有不会的题课下找他解答也总是有求必应。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喜欢上数学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年级期中考试我的数学是满分。

我们学校的操场比较小,跑一圈大概也就二百米。三年级时有早操,谢老师和我们一起跑操。别看人到中年,谢老师跑起来健步如飞,喊起口号也高亢嘹亮。冬天的早上,可能是在学校锻炼强度不够,谢老师还会带我们到村后的马路上跑步,漆黑的夜,迎面驶来一辆卡车,利剑般的灯光往往刺得人睁不开眼。他就让我们在高高的白杨树外边跑——那是人行道。再后来,他又带我们去田野里跑。
现在想来,那时的他真的很大胆,那时的我们真的很自由!
谢老师和我的父母都很熟,因为我们兄妹三个都是他的学生,况且我们还是有名的学霸级的三兄妹。还有,谢老师家的田地和我们村的相邻,每到农忙,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总会遇到谢老师。父母亲就亲切地和他聊天,我们在父母身后怯怯地喊声“谢老师”就不再说话了。
后来,我们上了初中,偶尔还会遇到谢老师,依然会亲切地喊声“谢老师好”。再后来我们渐渐离开了家,每年屈指可数的回家机会里也难得见到他。上次回老家听母亲说,前两年还见到谢老师,见面时他总是和母亲谈论当年的我,只是现在也见不到了。我心里突然觉得很感动:原来三十年的光阴逝去,我还在老师的记忆里,就像他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一样。
只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他还是否安康,是不是还能面带微笑地一眼认出我。也许这么多年过去,他已到人生的暮年,即使我再喊一声谢老师,他也漠然地没有了回应。谁知道呢,但愿远在老家的谢老师晚年吉祥康健。
二
初中时需要离开村子,学校离家也不算远。学生都是马路两旁村子里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由各自的村子走出,最后汇集到村后的大马路上——上初中的必经之路。
马路两边是满坡的野草,每到春来,那些野草都铆足了劲竞相开放。有红的像丁香花的酢浆草,有蓝蝴蝶似的阿拉伯婆婆纳,也有黄色的蒲公英,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小草花。它们似繁星点点,又似一块块绚丽的地毯,野花旁若无人、争先恐后地尽情地开着。
一路穿行在花海中是那时最美的体验。路南面的河湾里原来种了很多紫荆,收割后只留下遍地裸露的根,枝枝叉叉像无助的人在困境中挣扎。
有天早读放学,我们刚出校门不久就听到悠扬的笛声从远处传来。循着声音望去,在那大片盘根错节的紫荆根织就的土地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一袭风衣,面向南边迎风而立,手拿横笛在清烈的风中动情地吹奏着美妙的旋律。如果那场景用镜头来呈现,效果极像武侠片中的画面——辽阔的背景,主人公素衣飘飘,他手执长笛,笛声悠扬,那画面唯美而浪漫。

我想当年那个吹笛人应该是孤独的,那个年代喜欢音乐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凸显自己的爱好,似乎有点不合时宜——那是个内敛的年代。
初中的校园比较大,进大门是操场,进二门左手边是教学区。教学区有两个院,前院教学楼是初一初二年级,后院是初三年级。老师也有民师,好在也有不少科班出身的老师。对我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有很多,我印象深刻的是初二的语文老师。
老师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印象中,老师个子不高,肤色稍黑,方脸,两眼炯炯有神,步伐矫健。老师家离学校较远,经常见他行色匆匆地来到学校,又疾风般消失在人群中。即使看到他在校园闲庭信步,也总是愁眉紧锁的样子。
记得当时学习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老师范读课文,他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力求准确;很投入,因太过用力脖颈上青筋暴出。老师讲课很细心,所有的知识点都清晰地呈现在黑板上,课堂流程严谨规范,只是很少和我们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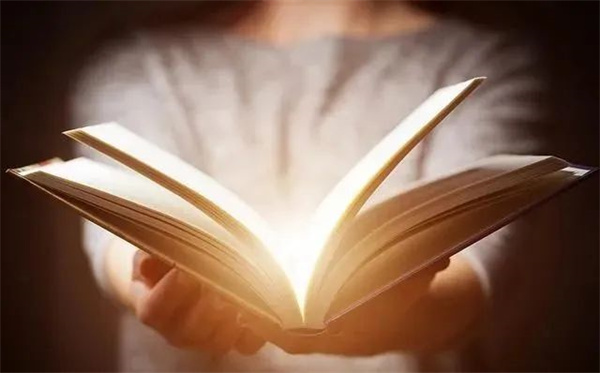
那时候的作文课,老师们都是先把写作要求布置下去,然后任由学生发挥去了。那时的我阅历有限感性不足,偏爱议论性的文章。有次作文课,我写的文章竟然成了范文。这大大激励了不擅长写作的我。
后来,我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是记心情,有时为了练笔,就这样我从中学一直写到大学毕业。直到现在,我当年的日记依然保存完好。偶尔整理旧书,随手翻看以前的日记就像破碎的时光又在手中复活了一样,当年的努力、奋激、喜悦……诸多心情一一呈现。
如果没有当年老师那由衷的赞赏,我的写作或者我的学习之路可能不会那么顺畅。也许老师当年仅仅是评讲作文的需要,无意中选中了我的那篇。可是谁能预料到一次不经意的表扬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呢。
三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老师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让我至今难忘。

如今,我也是一个在教育的百花园里耕耘了十八年的老园丁了。老师们当年的艰辛滋味也有切身体会,生活中的各种不易也颇有感触。但老师们在平凡中的坚守,在困境中的执着,在无人关注的一隅中的坚韧,时时鞭策着矛盾中的我。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们当年所讲的知识,我大都不记得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却成了我一生的滋养。可惜当年的我并没意识到这些,我们都成了彼此生命中匆匆的过客。我甚至在毕业之际都没想起和老师们说一声感谢,现在想来真是惭愧!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要对我所有的老师们真诚地说声:老师,节日快乐!

作者简介:
孙海英,河南省周口恒大中学语文教师。有诗歌、小说、散文见诸报端,惟愿以阅读为马,找寻精神世界的桃花源。有作品入选《师者行吟》。

- «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晓陌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