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多年前,在淮河边的那个小城,师父不仅跟我聊语文,还跟我聊家庭、聊男人,也聊育儿经。 北方的春天,柳絮纷扬,白蒙蒙一片。入夜,空旷的校园里,那些野猫亮开嗓子,细利如丝…… |
多年前,在淮河边的那个小城,师父不仅跟我聊语文,还跟我聊家庭、聊男人,也聊育儿经。
北方的春天,柳絮纷扬,白蒙蒙一片。入夜,空旷的校园里,那些野猫亮开嗓子,细利如丝线绕颈,哀切似最后一滴水渗进沙漠之眼。蓝晶、绿眸,密织了蒙蒙春雾,压在心头,闷得人喘不出气,还把人身上的热气全都黏到旷野,留下缕缕幽凉,在肌肤上游蹿。

这一晚,大家都没睡好。课间,师父就猫事传经,“昨晚,那些野猫叫得欢,闹得孩子翻来覆去睡不着,问我,这些猫在干嘛?” “是呀,猫想干嘛?”我此时的兴致里犹有昨夜的凉气。
“我告诉孩子,猫在寻找他的性伙伴。孩子沉默了,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两天前,一个深夜,我拥被而读。忽闻喵声欢实,忽高忽低,忽缓忽急,忽起忽伏。时而在南,倏忽往北。黄叶萧萧深闭门。隔离的日子,囿于一室,倒真像掖庭之罚了。寒气浸人,这声声猫叫,倒是剥出了冬的生机。
今天早晨,照例八点半下楼做核酸。花苔边的落叶,又厚了几分,踩上去,能听到“戚嚓”的声响。不远处,停着一只小鸟,没有捉到虫子,正在懊丧,也正在怀疑着。
回到十楼的小屋,阳光爬到东北角的墙上,两者亲密地扭打出一方暖意。此时,我必须大言不惭,做一个追光者。慢慢地,阳光往窗户边褪去,我紧紧跟着,一寸寸地移到窗户边。
正是这个时候,熬到下班的侯七,紧紧追着那白马上的男人和黑驴上的女人,闯过一个一个的红绿灯。过了新华门,驴上美人纵驴往路边跑去,停在一堵高大宽厚的黑砖墙前,她停下来欣赏一盆蓝花,她抚摸花朵上的茸毛。这时,一只碧绿的啤酒瓶子从天而降,落在了她的头上,弹跳了一下,落在了她的肩上,又弹跳了一下……
侯七在胡思乱想,有一个人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我当了皇帝,一定要下道圣旨,把乱扔啤酒瓶子的人手指剁掉!”
“你太温柔了!”另一个人说,“如果我当了皇帝,一定要下道圣旨,把乱扔啤酒瓶子的人剁成肉酱!”
“你还是太温柔!”又有一个人说,“如果我当了皇帝,一定要下道圣旨,把乱扔啤酒瓶子的人,做成一只啤酒瓶子!”

这么暖的时候,一只猫的叫声像一只炸裂的啤酒瓶子,穿墙而入,叫得我心悸,也叫得我心疼。一声比一声尖锐,一声比一声凄厉。它躲在某个角落,窥视着我,我看不见它。却可以肯定这只猫,并不是两天前深夜欢叫的那一只。叫了一夜的那只猫,已躺在语嫣拍的照片里。它像是睡着了,睡得很香。脑袋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此时,群里简直比长安街还要热闹。某君还在回忆,“那一晚上叫得我烦不住,扎实想闷一块石头过去。”某君即时拍手道:“逮到凶手了,就是你。”某君怒言:“怕是关疯了。”语嫣头像闪烁,“可以下来一位男老师帮忙处理一下吗?谁有不用的纸箱?”……沉默后,某君回复:“我有一个纸箱,就是小些。”
猫叫声又起,我再也没法跟着侯七继续追驴上美人了。我戴好口罩,拎起一个稍大些的纸箱,开门、锁门,往一楼走去。刚到九楼楼梯的转角处,眼前弱弱的一阵叫唤,像婴儿唤母。我顿脚抬头,前面太阳窗的台子上,卧着一只灰褐色的猫,身形较小。感觉到我的目光打量它,小猫立即向上蹿跳,然而,玻璃光滑,蹿了尺余,又迅速滑落,不及落地,便迅疾向八楼跃去。

猫的身骨灵活,天生太极高手,此番瞧见,确是真的。猫有九条命,怕是讹传或是我所不知道的某种编排了。
还未走到一楼,语嫣的头像再次闪烁--不必下楼了,已经处理好。我还是继续走到一楼,把那纸箱放置一个角落。实在抱歉,除去换洗衣物,我连一块布片都找不出。只好留给那只太极猫--姑且这样称呼它,一只空荡荡的“巢”。
午后,猫叫声犹如西风再次袭来。语嫣再度出手,这次,是为了救生,而非掩埋。这次,还有她和她。这几个妞在楼道里寻猫,从一楼觅至十楼,无果,又反向折回。一路上,给那只太极猫留下布施。噢,不,据其考证,应该还有另外一只猫,是它的同伴。
这天,太极猫一直坐在掩埋同伴遗体的地方,眼里蓄满泪水,如果人看不见它的时候,想必,它会用一只爪子,胡乱抹去滴落在胡须上的泪珠。如果我在那只猫还活着的时候遇见它,一定要送它们离开,一定要给它们备足猫粮,备足银子和利剑……
黄昏时,再无猫声入耳。想来,太极猫和它的最后一个同伴已然绝尘而去。那些楼梯转角处的猫粮,一部分动过了,大部分原封未动。

作者简介:
杨艳梅,云南省祥云县祥云一中语文教师。栖于杏坛,乐于文字。幸有作品见于报刊。有作品入选《师兴旷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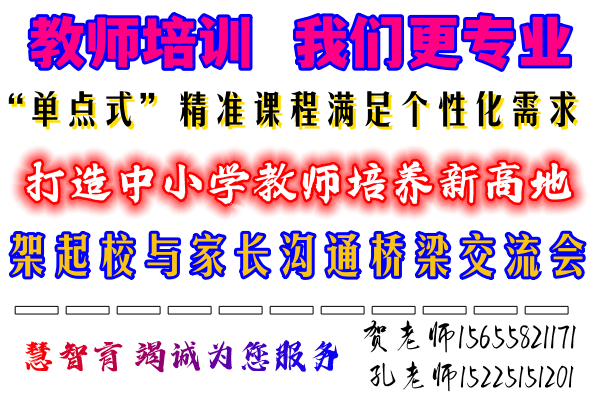
- «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木易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