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是彼时的专栏,抑或自己的周记,《此时众生》每七天写一篇,一篇不落,同样的长度,同样的情致,同样的节奏,将日常生活、所思所见慢条斯理地纳入其中,像自我沉思,又像与友…… |
是彼时的专栏,抑或自己的周记,《此时众生》每七天写一篇,一篇不落,同样的长度,同样的情致,同样的节奏,将日常生活、所思所见慢条斯理地纳入其中,像自我沉思,又像与友人叙谈,给人以亲切朴实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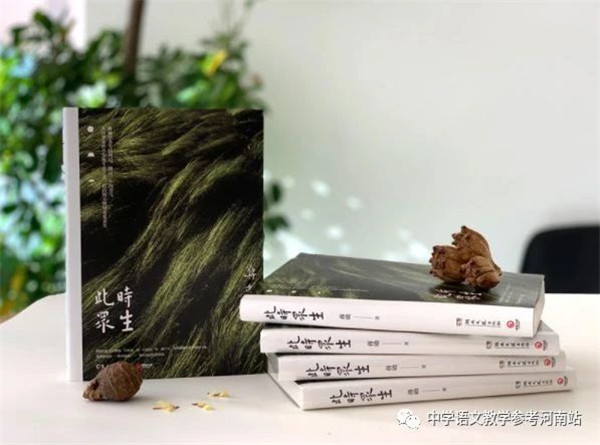
文中的“旋子”,如蒋勋《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的“丫民”,不知何许人也,却每于一声自然的称呼之后,就开始了他的分享和倾吐,窗外的鸟雀山林,日升日落,内心的喜悦忧伤,幻化成优美的语言和心绪,分享给远方抑或近处的好友。
相对于被人类涂改、修饰过的事物,作者更喜欢自然生发、芜杂率性的野性存在,他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带着天然元气的野溪温泉,他跑到偏僻的池上村去与广袤简洁的朴实大地紧密联结,他跑到无人的山谷,观看萤火在静谧的夏夜明灭闪烁,他在植物、动物和昆虫的世界里,回到遥远的童年,寻到“更单纯的本质”。他对旋子说:“旋子,生命存在的目的这么单纯。生命华丽或凄伤,也只是绕着这么单纯的目的打转而已。”
将美作为信仰的蒋勋毕生以美为志业,他讲述绘画之美,诗词之美,生活乃至生命之美,他为美感召被美震撼,他说:“‘美’使我们沉默,‘美’使人们谦卑,‘美’使我们知道生命同时存在的辛苦和甘甜,艰难与庄严。通过‘美’,我们再一次诞生,也再一次死亡。”
然而很多很多的时候,他看到贪婪淹没了素朴的信仰,他向旋子倾诉(又像是自语):“旋子,简单是不是美最基本的素质?”世间的美,艺术的美,时时感应着他,触动着他,面对美好,他也时常产生创作的冲动,突然的刹那,他说:“旋子,我想拿起笔来画些什么。”有时他就真的拿起了笔,将眼前的景致收入画中。某一日的黄昏,他对旋子说:“旋子,我此刻坐在石桥的护栏圈椅上写生,将近十点钟,夕阳的光在很远很远的城市西边的尽头微微闪动……”百无聊赖之时,他走到河边坐下,或者读书,或者发呆,或者沉思,或者,“静静看着水面上的日光或月光,一波一波慢慢流逝。”
瞬间惊叫的欣喜,归于沉寂的失落与怅惘,都是生活。蒋勋的文字就是从生活中出。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斯文儒雅,缓慢从容,真诚中带着一点淡淡的惆怅,点点意绪随着家常的叙说渲染开来,不知不觉中将读者带入某种氛围,和他一起沉浸,思索,欣赏,享受。写作即生活。驻足的时刻,他体察万物,有时也观照自身。面对都市的焦虑和疫病灾难,他说:“旋子,你或许会在街头看到我颓然独自伫立。”想象绝世美丽的秋日栖霞,他说:“旋子,我们都无言以对,不是吗?我们或者沮丧,或者无奈,或者毫无缘由地热泪盈眶,只是因为刹那间心里什么久未开启的地方被触动了。”心有所感,笔有所至,他的笔触细腻温柔,许多的思绪,被他敏锐地感知、捕捉。
书就该这样写吧?放下架子,放下腔调,回到生活、人性的日常,回到自心的真诚与纯粹。他的文字里,几乎不见地点,台北,巴黎,京都,塞纳河抑或淡水河,对他大概都是一样的吧,他在意的,是他彼一刻的感受、感知。
很多的时候,他与自己独处。

某一日,他“从人群中出走,走向山,走向海,走向久违了的自己。”断崖连接大海,他停车观景,“面向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汪洋大海,眼前没有任何阻挡,海阔天空,长风几万里吹来。生命可以这样飞扬跋扈,生命可以这样孤独,又这样自负。”他说,“旋子,我们或许已不容易懂得那样的孤独了。”深入的冥想,蓦然的孤独,使他领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壮美境界,明白为何长达千年的美术史,所有画里的读书人都在走向山水,他说:“不曾孤独过,不会读懂那一部美术史,对现世的权力和财富还有摆脱不开的贪婪,也不容易领悟一个时代,这么多的读书人走向山水的意义吧。”反观城市文明,他说:“旋子,一个进步的城市,也许不是只在追求越来越快的速度;一个进步的城市,也许要努力重新找回人类已经遗忘了很久、赤脚踩踏在沙地上的古老记忆。”
沿着东部海岸,他放飞灵魂,一路向南,大海在左,大山在右,让我想起昔日在台湾岛,自己也曾奔弛在这样的道上,从垦丁到台北,一路向北,奔走在大山大水之间,大山在左,大海在右,天地开阔,心地单纯,唯有欢乐。
某一日,他坐在野溪温泉的池里,眺望山下的都市繁华,他知道“繁华处正自喧闹,却与我无关”。
大河远去,他知道生命亦如此,不可重复,无法回头,不能挽留,但他依然全心地投入于生活,不愿错过生命中任何一个珍贵的片断,细小琐碎,对他也有意义。“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在细小处发现美,他随处发现美。立秋时节,他从地上捡起一片落叶,想要收存在用来素描记事的空白笔记本里,他与叶子对话,他为叶子感伤,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美是不是生命艰难生存下来最后的记忆?美是不是一种辛酸的自我完成?所以美使我狂喜,也使我忧伤。”秋分的街边他捡起一枚苹婆果,怀着好奇去探询它的秘密,作着他的思索,用自己的方式去觉悟生命的意义与庄严。

在一粒种子中,他都看到顽强的生命意志,“努力演化出最恰当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在太平山,他看石楠在初春开花烂漫,就像我在二道白河镇看胡枝子在仲夏开得喜悦明媚吧?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气馁,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蓬勃生长呢?“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何不回归自然,融入自然,顺应自然,欢喜此生呢?
某一日,蒋勋说:“我把面河的十二扇窗都推开了,窗外的河像一幅长卷一样展开……”将十二扇窗推开的刹那,我看到蒋勋的生活是奢侈的,置身闹市的我们,到哪里去推开那十二扇窗,到哪里去看到那长卷般欢腾铺展的河流呢?早上醒来,他看朝阳于明亮笃定的上升中宣告黎明的初始,接下来,他看日光在他的屋内一寸一寸地徘徊,一点一点地移动,待慢慢移至窗外,他就停止了工作,坐在窗台上看水……素净简单,却又奢华如此,谁说这样的人生不是上好的人生呢?生活,或许从未辜负过我们,阳光,大地,水,哪一样不是美好的馈赠呢?一切富足,都在眼前,都在素朴平常之中。
蒋勋说:“在窗台边看河,原来只是偶然。看书眼睛累了,或工作疲倦了,泡一壶茶,椅靠在窗台上,喝茶,看河水,也休息。”多么美好!简单奢侈,这也是我向往的生活啊。河面上一动不动的鹭鸶鸟,如一尊完美的雕塑,凝聚着心无所染、天明地澈的意志和内涵;窗台上两只飞临的麻雀檐下避雨,窃窃私语,意外的温馨和美好,都给他带来许多的喜爱和眷恋。
抬眼我的窗外,是高楼遮挡,空间逼仄,点点诗意,仿佛早已消失在了时间的深处,却也让我怀念起遥远记忆里的那一份生机盎然的人间烟火气。今年夏天在延吉,走出酒店的刹那曾意外看到了燕子翻飞,给我带来霎时的惊喜,在那里,我驻足了半个小时,安静地看它们在空中飞舞,小燕子翻飞着翅膀的姿态是如此地轻盈欢快、自由自在啊,瞬间将我带回到久违的童年。我指给先生看,先生的惊喜不亚于我,他说:“还真是哈,北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过燕子了,以前……”他讲起了以前燕子在家里筑巢,五线谱般停栖在电线上的诗意场景,勾起我更深的童年回忆,在儿时的姥姥家,张着黄嘴巴的小燕子在堂屋正中的鸟巢里,焦急地等待着衔食儿回来的燕妈妈……人与鸟,同屋共处,是多么迷人的场景啊!可是今天呢?老人去了哪里?燕子去了哪里?那童话般的童年,去了哪里?
蒋勋说城市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如“囚”字所指,每一个小小的空间,囚禁着一个人,“重重叠叠的‘囚’,高高低低的‘囚’,前前后后的‘囚’,‘囚’变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孤独的人们,有时扎堆结伴而行,用喧闹打发寂寞,蒋勋说:“现代城市的新伦理,在急切地与他人沟通之前,或许应该先学会回来和自己相处,学会独处的乐趣吧。”在一个近似禁锢又无力改变的空间里,我们是否也该像蒋勋那样,尽力地发掘、呼吸身边的美,比如,看着自己种植的一株株小花在阳光下一点点长大,比如,向飞临窗台的鹊鸟投去一抹欢喜的目光,比如,坐在树下的长椅上,打开一本自己喜欢的诗歌或散文,或者,如梭罗走在熟悉的小路上,沉思冥想,思索人生……是的,万境皆由人造,生活,原本处处充满了生机。
从小满到立夏,跟着蒋先生一起经历了春夏秋冬。他的文字平和,平静,带我去向远方,心灵的远方。(《此时众生》,蒋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2022年1月第7次)

作者简介:
陈艳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编审。著有随笔集《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漫漫经典情”丛书《艺术卷:美轮,美奂》《文学卷:且行,且歌》《哲学卷:觉知,觉醒》《自然卷:安然,安在》,“书之爱”丛书《书中岁月》《纸上情怀》,“书文化”丛书《书与人:随遇而读,自在欢喜》《书与城:家的记忆,生命的河》《书与生活:锦上添花,生活很美》《书与艺术:为美而生,与美同在》,“笺边琐记”丛书《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时光》《那些地方》《读懂美国:行走在现实与书本之间》等。作品入选《语文主题学习》《师意盎然》《师墨飘香》等多个选本。同时修习国画,作品入选“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当代五十位中青年作家书画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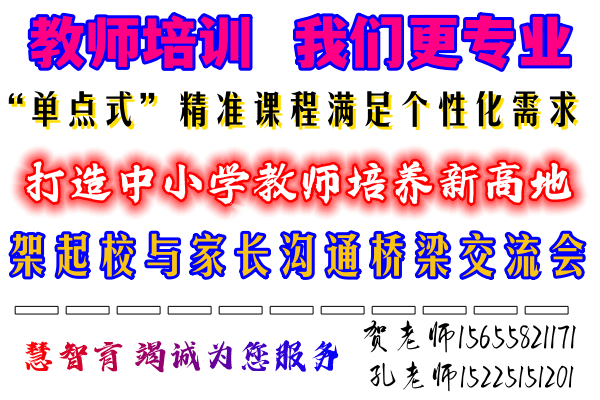
- «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木易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