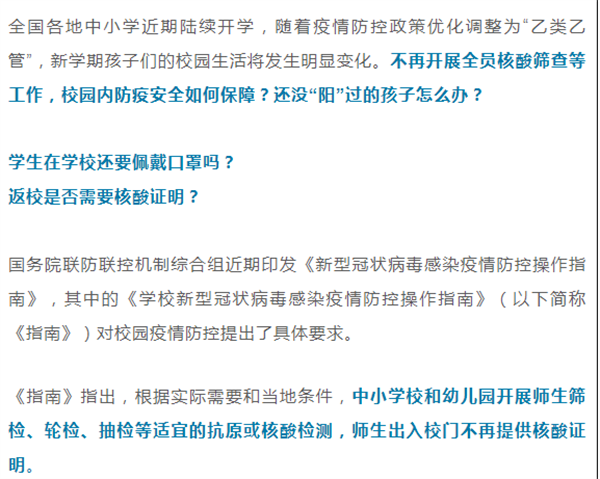| 摘要:为众人做饭之人,古往今来,似乎总不那么受人尊重与待见。其称呼中,似乎也带着些轻蔑与鄙视。比如火头军、火夫、老伙、厨子等。但也有例外:在村里,兼职在红白大事活动中,…… |
为众人做饭之人,古往今来,似乎总不那么受人尊重与待见。其称呼中,似乎也带着些轻蔑与鄙视。比如火头军、火夫、老伙、厨子等。但也有例外:在村里,兼职在红白大事活动中,给主家做饭招待亲朋的人,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通常尊称为焗长,或焗掌。鲁西南的发音不怎么标准,常念作焗jiang。至于含义与发音,并不怎么专注和研究它。
邻家有位老爷爷便是位焗长。他是淮海战场下来的解放兵。大跃进时候,在生产队的食堂里为社员煮饭吃。这一段饥荒时光,文学家称大锅饭,老百姓叫合大伙。

据这位爷爷说,所有的树叶,无论是杨是柳还是槐,无论是苦是涩还是麻,凡能爬上去够得着的,全被捋下吃光了。榆树更不消说,连皮都给吃进肚里去了。破败的村子望去,白花花没一点绿色,街上的路人,须扶墙才能行,否则便站立不住。
这样的艰难生活中,老伙们依然有着潜在的优越性:抛却的葱根、切下的菜疙瘩、枯黄半烂的菜叶等,都可悄悄给家人们充饥。自家的老婆,居然能和队长、会计家的女人一样,从肚子里下出个活仔来。“一人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人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此言不虚也。
村里的焗长,往往五六个一帮,集体行动。大一些的村子,可以有两三帮,基本上都男性,长幼不齐,甚至还有师徒传承。即便新社会吧,家庭里男女分工的传统还是有的:男人耕田翻地弄庄稼,唤做“外头人”,女人洗衣做饭喂鸡鸭,唤作“家里的”。

说来也怪,女人常年累月做饭菜,水平相对较高才对。可两性相较,却是焗长更胜一筹。谈论起这现象,有人说,女人都勤俭,不如男人舍得往锅里放油水。其实,煎炒烹炸的大锅菜,地地道道的手艺活,绝不是多放几勺子大油这般简单。
焗长受人尊重,在于没有架子,处处为主家着想。在农村,红白两事,都是家中大事件,一辈子也就是能摊上那么几回。若没有街坊邻居的帮忙参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主家往往全力以赴,重视的很。既要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又要让亲戚邻家吃饱喝足。得不得到好评不说,但至少不能差评。这重任,便实实在在的落在了焗长的肩上。
一个村子里,往往有几个经常替主家操心主持红白事的人,德高望重,思路清晰,通晓亲疏礼仪,被称作“照料事的”。正日子前两天,主家须把照料事的和焗长请到家里来,做两个硬菜。烟雾弥散、酒香飘逸中,后边的事情边吃边酌中便已商量。
预判当天能来多少亲戚朋友,预判街坊邻居能有多少来吃席,进而通算一下需要预备多少座。然后进一步确定一桌席上几个菜,几个汤,几个荤的,几个素的等,哪些菜自家地里可采摘,那些菜必须进城买……总之一个原则:既要有面子,又要尽可能地节省,尽可能的让客人们吃美喽。这,可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二天大早,焗长便带几个人进城去。一来焗长对八角茴香在行,二来与某些卖菜的熟悉且要好,不但真材实料,甚至还能便宜些。

早饭过后,其他街坊次第聚拢来。照料事的首先安排在主家或邻家的院子里垒砌大号锅台,然后铺摆人去租赁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本村没有的,辄到邻村去寻。今日先谈妥,当天便来取。
老邻老舍祖居多年,互相帮忙是分内的事,尤其是正日子的当天。熙熙攘攘的邻居称为“帮忙的”,照料事的叫他们 “忙客”。朴素的乡亲,常将客发音为“kei”,听上去更亲切些。
可不要小瞧这些普普通通、其貌不扬的人们,他们基本上是你在街面上为人处世的晴雨表。若日常为人实在太差劲,这茬口会立马被办丢人,尤其丧事时候,非得挨家去请下不得台来。那么事后多年,这家都要沦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和笑柄。
所以,无论你在外边混得有多粗,回到老家,都要将尾巴紧紧夹起来。大骡子大马值钱,人大了不值钱!乡亲们根本不屌你那一套。
忙客们漫不经心相互间插科打诨担水的、劈柴的、烧火的、剥葱的、捣蒜的、洗盘的、刷盆的,个个不亦乐乎。焗长们系了或蓝或白围裙,彼此简单分下工,便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忙活。便配菜的配菜,改刀的改刀。煎炒烹炸,各显神通。乒乒乓乓,锅勺交响。缭绕的雾气之中,飘散的香味之间,顾盼自定,谈笑自若,气质这一块儿,拿捏得杠杠滴。
在老家,吃席称作“坐桌”。红事包括娶亲席、回门席、祝酒席、生日席。白事包括热丧席和三年祭祀席。规模流程都差不多,档次亦逐年上升。现下,百十元一瓶的酒每桌两瓶,几十元一包的烟四盒,相较于七八斤白干便应付一场席面的贫困年代,真个是天壤之别。

接近晌午,召集大伙开席的信炮,是三个炸响的二踢脚。街坊亲戚纷纷将桌凳沿街摆开。一桌八人,先上塑料酒杯和筷箸,再上香烟与酒酿。最后,照料事的走上前台,代表主家对各位亲朋街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道几声感谢,说几句“少酒无菜,多多担待”的客套话,大席就可以开始了。
开席的菜品先冷后热,渐入佳境。端盘子的多是本门后生,满眼精神有力气,一溜锅台旁候着,双手端平了木质托盘。焗长熟练的用长把的铁勺将菜盛到盘子里,再将盘子放在托盘上。四盘一托,鱼贯而出,分送到每张桌子上。
四凉四热八个菜,便可以将桌子压住,足够客人们先喝上一阵子。此时,焗长们也略略稍歇,抽两支主家的香烟,抿一口主家的小酒,和旁边的忙客们唠两句闲磕。

估摸时候差不多了,照料事的便安排跑忙的,挨桌虚情假意让一遍酒。然后焗长便掐灭烟头,抄起铁勺,叽哩咣当,最后几个大菜一股脑上出,吃席的气氛达上高潮。
时代在进步,菜品在变化。小时候,只要农家地里能采集的,全都可以上席。比如豆角、黄瓜、茄子、白菜、萝卜、西葫芦,甚至还有笋瓜和搅瓜,总之素多而荤少。如今则大不同,烧鸡、粉肚加牛肉,肘子鲤鱼还别姬,多荤少素十二菜,还有两汤后面排。这舌尖上的变化,也可以算做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吧。
记得当年,吃席坐桌是令每一个人神往的事情。尤其是吃人家新婚前夜的夜席。天色将晚,空了肚子,十几个小毛孩儿,每人兑上毛二八分钱,兴冲冲到代销点买一副人物故事挂画,或一张山水风景玻璃匾,一串串姓名用自来水笔写好,便和哪些成年人一样,哄乱还羞着送到主家去,心安理得的在大门外边等候照料事的传唤。

一桌人吃完离去,下一桌迅速递补。吃席如流水,绵绵不断,故称流水席。这种席要赶早,可以吃到新鲜菜肴。因为其后的盘碟里,难免不会有上一桌剩余的残羹冷炙。即退桌子菜。尽管如此,大家仍吃得眉飞色舞,满口香甜。仗着胆子咂一口酒,差点没把腮帮子给咧到耳根子去。虽然死赔,主家仍喜上眉梢,满口客套。新房四壁重重复复的挂画和牌匾,一挂几多年,任他蜘丝蛛网,蛀啃虫咬。
我们村的焗长,有几个凉菜十里八村特出名:大大的醋蒜,大大的麻汁,大大的香油,黄灿灿的鸡蛋饼切细,金针菇或黄瓜丝配入,双手大盆里几番操弄,抓到盘子里,看一眼都让人垂涎欲滴。其实,盘子底最终的干净程度,才是他们手艺最直接的得分。虽然表面上不说,心里在乎的很哩。

待得人去桌空时,跑忙的便抬几个大盆,将吃剩的热菜和凉菜分别合在一起,收拾残局。一桩心事落地,主家长出一口大气,唤作“客走主家安”。然后,让焗长将预留的食材,施展几分功夫,溜溜煎煎,烹烹炒炒,和跑忙的一起,上酒支桌重开宴。觥筹交错之间,感谢与仗义之中,疲态尽去,很快进入微醺状态。
夕阳西下,大幕将垂。焗长们围裙裹了心爱的菜刀,一番推推让让之后,拎着主家赠送的两瓶好酒,揣几盒硬塞兜儿里的香烟,蹒跚了步履,红着脸膛走向家去。遇上站街的邻居,话多的焗长会晃晃着立个不住,啰里啰嗦唠上好半天。
盆里的大杂烩,由女人和孩子抬着,挨个经过邻居家门前,粗瓷大碗窊了,一家一碗分送。既不浪费,孩子们还能解馋。几十年过去,哪些嘴巴子下的杂菜,仍是记忆中的佳肴,哪怕还留有一丝残酒淡淡的味道。

焗长们都深谙传统的礼数。这礼数表现在对主家当日最尊贵的亲戚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比如婚宴,娘家人自然最尊贵,尤其相送的男客,哪怕只是个孩子,都要安排主桌上坐着。男方早预备了几位族中长辈相陪。因为是主桌,自然要比街筒子上多出几个菜来,品质也高些。陪客的不是让烟,就是劝酒,极尽殷勤便是;娘家人个个表现着谦虚,生怕将酒用过,生怕将话语说错。毕竟除了吃喝,还代表着娘家人形象不是。
三天后,娘家兄弟请新娘子回门,夫君要一路同去,称作请新客。当天,还要一名善饮的“喝将”随行,唤作盒子腿。因这是金龟这辈子在老丈人家最尊贵的一天,故气氛隆重得很:八仙桌必须有,太师椅必须有,椅上一床红棉被必须有,酒壶酒盅必须有,茶壶茶杯必须有,哪怕是你东寻西借的。金龟老老实实正中椅里坐,周围亲戚长辈围圈陪,派头算是给足了你。妇女姑娘多闲暇,大门口拥挤着,伸长了脖儿向着屋里探看,嘁嘁喳喳弄两句评价,俗称看新客。

简短的几句嘘寒问暖客套话,便添茶开酒菜上桌,喝将起来。小龟子表现得斯文而腼腆,虚伪而少言,多是怕酒后言多,言多必失,失则洋相出,给不了人们好印象,故由了他的自便,不怎么劝他。可怜盒子腿成了桌上的名牌。三五圈过后,便挨个向其敬起酒,发起进攻,进入状态。盘子一个一个源源着上,摆不开就层层摞起来,因数量多而显得诚意足,酒杯一次一次碰将起来,理由也是个千奇百怪,因敬得勤而觉得情谊真。
这桌菜,对焗长很是一种考验,不但味道美,花样多,更要弄几个可显摆的出来。如什么拔丝苹果琉璃馍,糖醋里脊活眼鱼等。村子里请新客有不成文的规矩:非得夕阳西下,方可放新客还家,否则,便仿佛招待不周到。但是,如此拉长的喝酒战线,敬酒颇废人力资源的。喝到高潮处,街坊来敬酒,村学校长来敬酒,村长支书来敬酒,即便忙活了半天的焗长,也同样可以来敬酒。
最后的节目是上点心。先前的酒菜全撤去,吸烟喝茶重新来。点心都是起始作陪的人带来的,一次上一盘。端盘的后生先报出这盘点心的主人。新客起立作揖要求主人家转转相。主人则谦虚的说不必啦。然后,新客从中夹那么一两筷,放在专门的碟子里。如此重复,直至终结,手帕包了,带回家去。

红红的太阳要坠下去,热闹的场面也终归静下。新客和盒子腿,各推了自行车,渐渐出了村子,扭扭歪歪,迤逦而去,消失了身影。据说,一出村,兜肚连肠喷涌而出的有,连车带人一溜下沟的有,斜躺路边呼呼酣睡的亦有。总之,当年那个年代,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焗长永不缺热心肠,但同时必须兼有一副铁心肠,尤其热丧时候。不消说裱糊的牌楼摇钱树,草扎的金牛五花马,单是竹帘掩映灵棚前, “灵柩未入三尺土,哭声以上九重天” 的对联,便将空气中饱含了哀伤沉痛气息,更哪堪一腔唢呐凄厉。“宁隔千里远,不隔一层板”,最贴切的描述了。
先是一拨拨街坊邻居兼亲戚前来吊唁,拈香奠酒行九拜之礼,灵棚两侧的白衣孝子伏地配合几声哭泣。邻近晌午,重头戏开始,即重孝的子女祭祀。所谓重孝,非至亲不可以穿戴,且必须又脏又破。在架孝的搀扶下,一道长声“举哀——”孝子便手握哭丧棒,哇一声大哭,直上云霄。为将巨大的哀痛淋漓的表达出来,要边哭边说,声调拉长,抑扬顿挫,实哭似唱,泪眼婆娑,鼻涕老长,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有资格祭祀的包括儿子儿媳和女儿,行二十四拜礼数,故用时较长。不必担心剧痛之下礼数是否周全,架孝的一个个给数着哩:向上提,孝子即站起举棒,向下拽,孝子即跪地扣头,只管放心哭唱便是。村妇老太娃子低趣味,无悲无喜拥挤着看,偶还窃窃私语,毕竟生前不孝,死后嚎啕表演的也不是没有。
祭祀环节结束,架子会上场。架子会系专门用组对好的木架将棺材抬进墓穴的自发组织,年轻力壮,听命于架子头。待得亲人们完成对三长两短内最后一撇,众人吻合了上盖,斧子锤头砰砰乓乓楔子钉牢,真正的盖棺定论,与世隔绝了。
各就各位后,架子头啪一声棺头猛击一掌,众劳力一声吆喝——“起”!你拥我挤,竭尽全力,慌乱紧张中,将棺木抬出,固定在当街的架子上。待得长子长孙将盛有浆子的小瓦盆,砰一声架子上摔稀碎后,大伙齐刷刷杠子上肩,在越来越弱的哭声中,急匆匆向新打的墓地行动。

至于哪些香车纸马摇钱树,早给孩子们或拿或抬提前送往了目的地。这活计不是白干的,每人至少两毛钱小费,出发前由主家给出,先钱后活,不带赊账的。
焗长实实在在的见证着整场的悲伤,若没点儿硬心肠,悲悲戚戚,泪眼朦胧,怎不影响手艺的发挥?稀里哗啦的泪水都撒在菜肴里,让人怎得吃?
村子里的人们虽穷了些,面子还是看重的。一般都要请一班响器,即吹喇叭的鼓乐班子。他们不但能将喇叭吹得天地同悲更渲染悲伤色彩,也能将芦笙竹笛合奏出百鸟朝凤热烈欢快。其实这帮家伙才是四里八乡监管悲喜的铁石心肠。同样要一座酒席伺候,曲终人散后,手指查点了钞票,袋子扫荡了桌上所有,扬长而去了。
起初,很不理解为什么主家大丧,桌子上的人们却仍然连吃带喝,不受影响。后来才知道,能顺利的让逝者入土为安,安然长眠,对谁不是如释重负呢。后来高中学语文,读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更多了一层感慨。

现下的农村,光景比当年不知好出多少倍,喜忧大典的事情仍年年岁岁。但焗长的光环却不争的渐渐褪去,生意惨淡,日薄西山。现今,他们已被专业的“包桌”所代替。“包桌”更全活更专业:自带灶具,自带食材,自带桌凳,自带服务员,主家扫码结账便了。
尽管如此,村上仅存的几个老焗长,仍让我感到亲切和钦佩。他们的手艺仍是最棒的手艺,他们的菜品永远是三里五村,乡亲中心里的头牌!

作者简介:
俞海英,现供职于山东省东明石化集团。勤工作,能田亩,喜太极,乐文字。本事不长年岁长,挣钱不多花钱多。虽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多不接近,仍抚掌旧年顽劣之事,不作目下消极颓废之状。有作品入选《师心有痕》《师者行吟》《师意盎然》《师墨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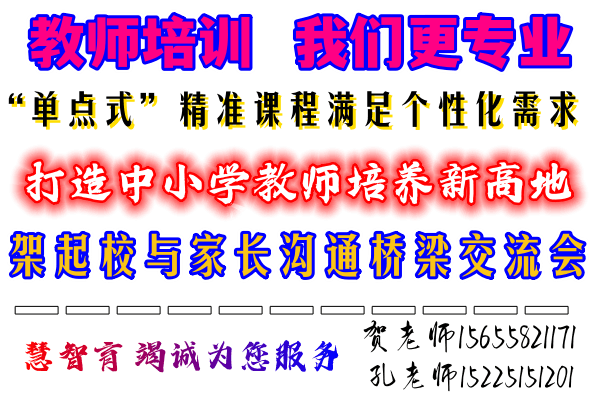
- «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晓陌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