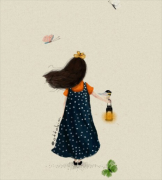| 摘要:孩提时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天蓝蓝,水清清,中国大地没有半点儿污染,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化肥、农药。人与动物的生活环境差不多。猫、狗这些皮毛动物身上有小虫子…… |
孩提时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天蓝蓝,水清清,中国大地没有半点儿污染,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化肥、农药。人与动物的生活环境差不多。猫、狗这些皮毛动物身上有小虫子,人贴身儿内衣上也生虱子、跳蚤之类的小东西。
我们小孩子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课堂上,老师正讲得带劲儿,自己津津有味,听得着了魔。突然,肚子上、肩膀上似乎有小虫子在蠕动。“哎呦”竟然敢下嘴,咬老子一口!嗬,不知悔改的的家伙,又咬一口。于是大怒,把胳膊悄悄伸进内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拇指和食指所形成的“钳子”,只那么轻轻一捏,就捉住了。于是,把这只米粒大的虱子“发配”到作业本上,钢笔尖就成了“刽子手”中的“屠刀”,慢慢“折磨”起这只不速之客。
这种游戏“传染”得很厉害,后排的几个大个子也聚在一起,早把听课的事抛在了脑后,一个个在肚皮、后背上胡乱“搜索”一番。你一只,他两只,放在一堆儿,居然看起了“虱子大战”!那场景、那盛况,不亚于今天的孩子玩电子游戏。
插入“捉虱子”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年月,中国大地特别原生态,人与自然是无私的、干净的、友好的、一体的。
大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国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一街两巷,一户挨着一户,一家连着一家。正房、厢房全是土屋,土坯土墙,上盖是用黏泥和麦秸(或稻草)一层一层铺上的。住上几年,屋顶上的瓦松、狗尾巴草郁郁青青,别有一番诗意。
院子里东南角是厕所,紧挨着是猪圈、狗窝、鸡窝、牛棚一字排开,就连泥土堆砌的矮墙也不闲着,深秋时节,上面爬满了眉豆或丝瓜。老枣树的枝杈上挂一个鸟笼,里面要么是百灵、画眉,要么就是鹌鹑。在鸟笼的旁边,肯定还有一个用高粱秆子扎成的形如葫芦一样的东西,那是孩子的爱物——蝈蝈笼子。
居家过日子,自然就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了。夏日时节,野草疯狂。隔三差五,一场透雨过后,一夜之间,野草就会长高一大截。
我小时候,七口之家,二十多亩地,父亲、大姐扛上锄头,锄完东地,锄北地,锄南地。一轮过后,再回到东地一看,野草盖过了庄稼。两张锄头披星戴月,就是锄不完田里的野草。
下了学,打完了猪草,架上蝈蝈笼,拿上砖头蛋子磨成的陀螺,找伙伴儿玩上一阵子。东南角的楝树梢上早挂起了月亮。一时炊烟袅袅,露水沉沉,就听到母亲的喊叫:“三儿,去东北地接接你爹,饭都快凉了,咋还不下晌!”领了“圣旨”,就撒开脚丫子就往地里跑。出了村,就嗅到庄稼的香气、泥土的香气,还有蟋蟀、蚯蚓的吟唱,整个大地小径纵横,庄稼萋萋,层次分明。
仰头看天,残月如弓,繁星点点,黛蓝的夜空那么清新,那么透明,光凭肉眼就可以分辨得出牛郎星周围有几颗小星。
走不多远,摸摸头发、衣服早被露水打湿了。转过一座石桥,就听到“拖沓拖沓”的脚步声,时不时传来几声“干咳”,那是爹抽纸抟豆叶子香烟所发出的喉管动作。双手围成“喇叭筒儿”,搁在嘴边,扯开嗓门儿,杀猪似的喊一声:“爹——”
“三儿,你姐给你捉个小兔崽儿,我又给你逮了两只青头蝈蝈。快过来看看!”这是爹的声音。
“弟弟,快点儿,小兔子在我怀里踢腾呢!”这是姐姐的声音。
我紧跑几步,一手拽住爹的手,一手拉住大姐的衣襟,在月光下,在蚯蚓、蟋蟀的歌声里,诉说着一天的相思,一天的见闻,一天的劳累,一天的收获。
……
农耕时代,真如陶渊明诗句里描绘的那样:“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是位纯正的儒家。我喜欢充满田园气息的“人境”,感觉得很亲切。这两句诗就是两幅画,活画出了“乡村小巷人家”,很温暖,很亲和,很熟悉,很留恋,也很向往。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它代表一种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可以是人生境界、生活境界,抑或是教育境界。
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那种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禁锢的“鸽子楼里”,告别的不仅是清风明月,草长莺飞的泥土气息,更重要是没了自然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是人们在虚拟的电视、电脑、手机世界里,为功利所役,以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追逐名利,追逐潮流,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如今,大地上的一切全是病态的:蔬菜是沾了农药的;猪肉、鸡肉是掺了添加剂催成的;天空是雾霾横行的;河流成了生活垃圾的集散地。就连呼吸的空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人们离家出行不得不戴上口罩,架上眼镜……泥孩儿,泥孩儿,孩子一旦脱离了泥土,生活在“病态”的大地上,禁锢在楼房里,没了星星月亮,没了捉蝈蝈、斗黄鼠狼,没了昆虫,没了小鸟,没了红花绿草,没了小溪歌唱。长此以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们教育工作者整天高喊“为孩子提供有营养的课程”。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我们的生活方式,有“营养”的课程,我们该如何提供?教育的回归?难!难!难!
有人说,教育是农业,孩子就是庄稼。那么,我们教育工作者就是农人。我们得尊重孩子的天性,如同农民顺应四时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农人侍弄庄稼,投入的是真感情,行动起来是真呵护。
“天、禾、人”合一,是农人的高境界。
“教、学、做”合一,是否就是教育的高境界呢?

作者简介:
梁泉清,山东省东明县第四实验小学语文教师。与书结缘,神安、心安、教安。曾作自嘲诗——“写作教书吃饭,粉笔讲台黑板,师生朋友习惯。永不自满,挑战自我非凡!”
- «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娜娜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