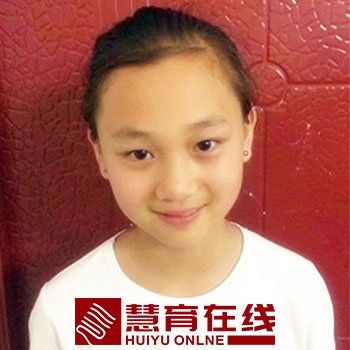| 摘要:前两天,老家邻居刘老先生寿终正寝,享年84岁。刘老先生原系单位职工,与家父同事,为人豁达,乐观,在左邻右舍中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老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故此…… |
前两天,老家邻居刘老先生寿终正寝,享年84岁。刘老先生原系单位职工,与家父同事,为人豁达,乐观,在左邻右舍中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老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故此,我决计多回去几趟,帮忙做事,尽桑梓情谊。
办丧事最隆重的仪式是出殡,一般说来,选的日子不是排三,便是排五。三五天忙乱,将亡人送走。可见人世间,养儿育女辛劳一生,就这几天让儿孙忙碌。家族内的,未出五服的跑前跑后:张罗祭奠物品,采购招待乡亲的各种食材。出殡当天,乡邻前往送葬。如今办白事只要花钱,礼仪公司和流动餐饮服务就解决了难题。
我所能做的,无非是抬桌椅,写挽联。当年,刘老先生健在时,常见他在村里红白喜事中做礼桌。他是乡邻中少见的,能用小楷毛笔写一首端庄的隶书字的。如今,我也要提起毛笔了,我实在是有些心虚的。
写挽联大有讲究,今天才知端详。
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司仪,他姓张,五十开外,国字脸,脸上几颗痣,鬓角斑白。刘家人让他和我张罗写挽联的事,他自述经历:出身民师,原先教过几年语文,能说会写。后来到耐火厂干,又转行做司仪,专业主持丧葬礼节活动。
张司仪看我戴着眼镜,问我做何营生,我答到,和你先前一样。他便让我帮他写灵堂的牌位,我准备叠白纸,他看我的动作笨拙,还想把一张大白纸割开,便说不能这样做,要用整张纸,他三下五去二折叠白纸,用毛笔写了几行大字,起笔轻落,顿笔回锋。我一看,便知此人书法有几分功底。
张先生又给我讲了一些写牌位的规矩,比如有些乡镇只写家祭二字,还有挽联常用词语。我做聆听状,以示虚心。实则感觉他的好为人师,很多时候,我也如此,想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所在。张司仪又拿出他写的祭文,我粗看一下,发现这祭文竟然全部押韵,将刘老先生的一生概括的淋漓尽致,而且通俗易懂。我没敢说出自己是高中语文教师,因为我知道,我只能讲诸如《祭十二郎文》《祭妹文》这些文言文,却不能写出如此接地气的祭文来。
我问道:“张先生,您是否了解刘家情况?”
“那当然,我前两天,专门听刘家说了一个小时,自己又熬了半夜。”
开始举行祭奠仪式了,张先生确实有两下子。刘氏宗族人员众多,他头戴礼帽,穿一袭长衫,手执佛尘。声如洪钟,大家在他的指挥下,一轮一轮的跪拜作揖,进退有仪,秩序井然,真是江湖亦有道,术业有专攻。
张司仪拿出他写得祭文,开始诵读:他读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刘家亲人听得悲悲切切,女人们哭声一片。往常,围观的乡邻闲谈热议,四处走动,早已见惯。陶渊明有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嘛。今天,天气虽热,气氛肃穆,但闻唏嘘慨叹之声。
礼毕,刘家一位大哥来和张司仪攀谈,问道:“师傅,该给您多少钱?”张司仪说:“一百二百随意。烟两盒,酒两瓶,你看着办。”刘大哥说:“我给您三百元,两条烟,两瓶酒,您别嫌少。”旁边的乡邻,有人开始打听张司仪的电话。
张司仪的事,让我想起柳宗元的一篇文章《梓人传》。张司仪善于表达,又会组织,以自己能说会道感染众人,调动大家的情绪。可以说也是适应社会,自力更生,有一技之长的人啊!

作者简介:
丁伟奇,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语文教师。任教二十余年,雅好读书,怡然自乐。
- «
穿越到手机上阅读
● 编辑 : 娜娜 / 小威 / 沈晓沫
● 发布 : 娜娜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