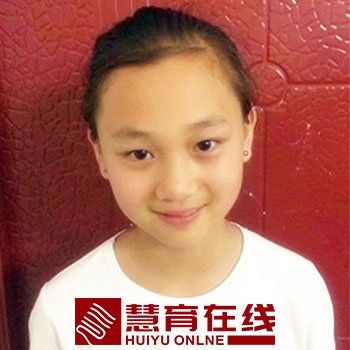| 摘要:大队的“小”学校设在去俺们村的路口,从俺家里出来爬过一道陡坡,再往前也就是半里多地。冬天的时候,一块儿热红薯吃完差不多就到了。 “小”学校最早只有小学,后来又有了初…… |
大队的“小”学校设在去俺们村的路口,从俺家里出来爬过一道陡坡,再往前也就是半里多地。冬天的时候,一块儿热红薯吃完差不多就到了。
“小”学校最早只有小学,后来又有了初中,后来就只剩下小学,再后来小学撤走了,到现在连影子也没了。
“小”学校真是小,起初只有几间教室,土坯房,矮矮的。“课桌”是用宽窄不一的桐木板或杨木板搭起来的,从自家搬来的高高低低式样不同的小凳子摆放在下面。墙角有土坯垒成的煤火台,烧散煤的,冬天取暖。后来有了初中班,新盖了几间教室,红砖墙,红瓦顶,红门窗,扯上了电线,安上了40瓦的灯泡,亮堂了许多。“课桌”变成了水泥预制的,水泥桌面,水泥桌腿,趴在上面读书夏天凉冬天冰,一双手年年遭罪长冻疮。
“小”学校坐北朝南,门口是一片不大的空地,权做操场。操场边一条土路通向村里,沿土路边是一道不宽也不深的水渠,除去冬天,整日流水潺潺。放学的时候,俺们常常叠几只纸船,插上草叶放进去做帆,“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小”学校院墙的东面和北面是桑树园。这桑园不管对村里还是对小孩儿都是稀罕地儿。清明前后桑树发芽,一入夏就枝壮叶肥满树浓郁,村里的女人们有的就采来桑叶喂蚕,孩子们渴盼着摘桑葚。桑葚起初是青的,不中吃,刚泛红的时候是酸的,也不中吃,只有长到红得发紫的时候才是最美的味道。然而吃多了也不好,容易上火流鼻血。村里种这片桑树是做桑杈用的,当它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就让它分岔丛生往高处长,等到七八尺高手腕粗细时便砍下,经过剥皮、烘烤、整形,加工成轻便耐用的桑杈,作为本地的土特产销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甚至东南亚各国,成为村里一笔不小的收入。
西边的院墙外是几家农户,有高大的槐树和桑树伸到院墙内,闻得见槐花的清香,看得见诱人的桑葚,却因为太高够不着没有福气消受。
俺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里有俺曾经的老师。
现在看来,俺这些曾经的老师既不是文人笔下的春蚕,也不是诗人笔端的蜡烛,更没有太阳耀眼的光辉。在俺的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平常的农村人,一群挣工分拿补贴的庄稼汉,谈不上渊博的知识,也没有扎实的专业素养。要是他们身上没有老师这个身份,也许俺应该称呼他们姐姐哥哥叔叔姑姑或其它什么的。
待俺最好的是位女老师,名字叫张璞妮,家是本大队的。大概在俺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俺随母亲去湖北襄阳父亲的部队探亲,回来的时候功课已经丢下了一大半。即使这样班里测验的时候俺的分数也不是太难看,可她却坚持每天下午放学后把俺和另外几个不济事的学生留下来一块读课文写生字,直到她满意了才算罢。多年以后她出门了,每次回娘家都会经过俺们村,母亲碰见了就会喊住她说说话歇息一会儿。
有个最厉害的老师叫满仓,姓张还是姓赵俺忘了。他没有教过俺,俺自然不知道他课堂上是啥样。倒是有几次在课间看到他训斥三喜叔,训着训着就骂开了,那语言真是既生动又形象,句句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恁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真是个甜汤泡皮球糊涂蛋!”
“你来学校弄啥来了?你是屎壳郎爬到鞭梢上受悠来了?”
那时候后的孩子哪敢犟?都被骂成这样了回家也不敢给大人学嘴,害怕再遭家里大人一顿臭骂。从此以后,见到这个满仓老师俺就躲着走,虽然俺没招他没惹他。
班主任王老师也可厉害,不过这个“厉害”是有本事的意思。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教俺物理和化学,教得好不好没法评判,因为没有可以比较的对象。俺学得不算最好,因为他没有教会俺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
王老师的“厉害”在于他没有右手却能写出不赖的字。
王老师的右手据说是让雷管炸掉的。他家门前有一座小水库,王老师用雷管炸鱼,鱼没炸着右手给炸没了。想起来一定很疼,也很后悔。
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右胳膊蜷着,左手高举,捏着粉笔搭在黑板上,脸向左边侧着,眼睛的余光扫视着讲台下的每个人。他的字流畅耐看,行笔的速度也很快,很难想象他是咋练出来的。
那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练习册,王老师就给俺们印页子。手推油印机、刻字钢板、铁笔、蜡纸,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王老师趴在水泥乒乓球台上,钢板上蒙上蜡纸,手握铁笔,仍是向左侧着脸,不消半节课就成了满满一版。把蜡纸拿起来对着光线看,一律的仿宋字,细长秀气,有棱有角,大小匀称,行是行列是列,爽心悦目的。
音乐老师有点招俺烦。
说是音乐老师,记忆中不记得他教俺们唱过什么歌,更说不上教乐理知识了,兴许他也就不懂什么乐理知识吧。唯一记得的是他会拉弦子,哼哼唧唧的,不知道是什么调调。
烦他是因为他逼俺唱戏,唱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段《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兵》。这段戏俺会唱但俺不愿唱,一是因为俺天生腼腆,不想在人群前露脸,二是俺配合不好他拉的弦子。
有一次确实烦了,晚上排练的时候俺故意不去学校,他竟派了俩同学到俺家喊俺。喊俺也不去,俺哄那俩同学说肚子疼可难受,请上一次假吧。
最后要说说俺的语文老师。
这要从一个笑话说起。
有一天语文课,照例是先挑学生到黑板前默写头一天的生字和词语。同学们照例是提心吊胆的,“千万别挑我,千万别挑我!”上过学的人都有过这种心思,你知道的。
一男生一女生俩倒霉蛋被挑上了。他俩磨磨唧唧上了讲台。
男生默写的是“万水千山只等闲”,女生默写的是“苦干加巧干”。
这俩货兴许是吓坏了,男生不会写“等闲”俩字,抖抖索索画了两个“〇”,而女生把“干”写成了“杆”。
语文老师冷眼看了好长一阵子,终于发话反问了:
“苦杆儿加巧杆儿是什么杆儿呀?”
“万水千山直瞪眼儿。哪红军战士还怎么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啊?嗯——!”
一声“嗯——”吓得讲台上的俩人低下了头,一声“嗯——”问得讲台下的俺们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难受。
这个场景到现在俺还记得清清楚楚。
俺从语文老师那里学到的最扎实的东西是汉语语法,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不光是会背概念,还会到讲台上替老师给那帮糊涂蛋们讲解分析。现在的老师大都不用讲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的学生甚至一些年轻教师写作文做文章都分不清“的地得”这些结构助词的区别,如果你指出了他的疏忽,他还会满心不高兴地说:现在都不管这些了,可以通用!让俺半晌无语。
俺这些曾经的老师有的很幸运,在随后的日子里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端上了铁饭碗,成了身在农村的“国家人”。有的却因为年龄的关系或是自身的业务能力,离开了“小”学校,回归田园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平淡日子。
而俺,只能站在曾经的“小”学校所处的这片旧地上,小心翼翼地触摸斑驳模糊的点点记忆,一遍遍谛听渐次逝去的遥远的回声,用这些笨拙的文字表达对它和他们永恒的敬意。

作者简介:
刘书民,新密市兴华公学语文教师。信奉:人生在世要不断地修炼自己,否则就会被天地所不容。
- «
穿越到手机上阅读
● 编辑 : 朤朤 / 陌语 / 沈晓沫
● 发布 : 娜娜 审核 : 朤朤 / 陌语
● 热线 : 158-1078-1908
● 邮箱: 770772751#qq.com (#改为@)